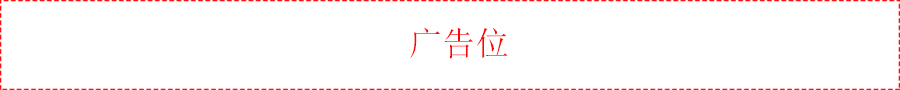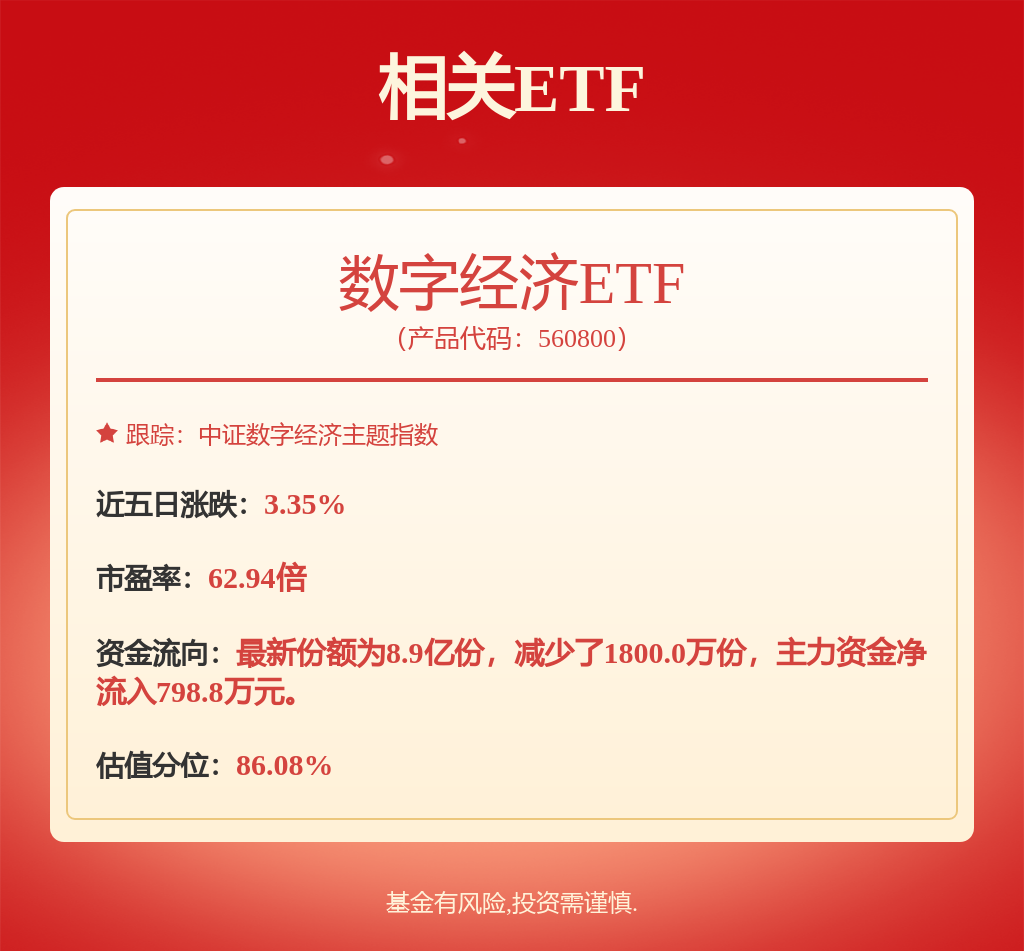日本经济在1990年前呈现出虚假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货币宽松+信贷扩张”导致资产价格膨胀 ,企业/家庭过 度杠杆化。日本经济看似繁荣,实则积累了致命隐患。货币宽松与信贷扩张:1985 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1985-1988 年日元对美元升值 110%),严重冲 击出口。为对冲影响,日本央行持续降息(基准利率从 1985 年的 5% 降至 1987 年的 2.5%),释放大量廉价资 金。 资产价格疯狂膨胀:宽松资金涌入房地产和股市,形成巨大泡沫。1985-1990 年,东京房价上涨 3 倍,1990年巅 峰时东京都房地产相当于当时全美国的总地价,日经 225 指数从 1985-1989 年涨幅超200%。市场陷入狂热。 企业与家庭的过度杠杆:银行盲目放贷,企业通过 “交叉持股” 炒房炒股,家庭则加杠杆购房。1990 年日本企 业债务占 GDP 比例达 140%,家庭债务占比超 60%,远超同期欧美水平。
日本股市在1990-2024年间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日经225指数和东证指数为基准,可划分为三个 主要阶段:快速下跌期(1990-1992年)、震荡下行期(1993-2012年)和恢复走强期(2013-2024 年)。其中震荡下行期又可再分为1993-2003的下行期与2004-2012的震荡期。 日本指数至今涨幅萎靡,日经225指数从1990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4日仅上涨2.51%,东证指数甚至于 下跌3.35%。相较于标普500的1564.3%,表现萎靡。 30年间,日本两大指数近乎没有变动,这与前大半段的指数长期下跌趋势有关,背后更折射出日本时代困 境,经济政策,外部环境等因素。
核心矛盾:资产价格暴跌,原本依靠资产膨胀扩张负债的企业和家庭突然面临资产负债表严重错配:资产 缩水而负债沉重,净资产为负。这直接触发了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原本用于投资扩张的现金流被 迫优先用于偿还债务,出现了“偿债>投资”的反常局面;与此同时,家庭也出于资产缩水和对未来收入 悲观预期,选择主动去杠杆、压缩消费。这种“双去杠杆”行为导致整体私人部门需求塌陷。 资产泡沫破裂 → 企业/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 → 主动去杠杆 → 投资和消费同时下行 → 总需求萎缩 → 经济 持续低迷 → 市场信心进一步受挫。 政策失误:1989年开始日本央行为了抑制泡沫连续5次加息,使官方贴现率由2.5%升至6.0%,直接击穿股 市与地产泡沫,1991年降息滞后。
市场表现:1990年,日经225指数下跌38.72%,东证指数下跌39.83%。为历史最大年跌幅。 日本经济:经济虽增长但结构失衡,表面维持增长,但主要由房地产和金融投机驱动。制造业出口受日元 升值持续压制,实体经济空心化加剧。通胀与资产价格背离,1990年末CPI 同比达3.8%,但核心通胀仅 1.2%,反映物价上涨主要源于资产泡沫传导而非需求扩张。 政策动向:货币财政双紧缩,1989-1990年日本央行连续5次加息,政策利率从2.5%升至6.0%,直接推高 企业融资成本。1990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年初6.44%飙升至9月最高峰值8.05%。1990年4月大藏省实 施《土地融资限令》,要求银行房地产贷款增速不超过总贷款增速,切断投机资金链。同时消费税从3%提 至5%以抑制消费需求。
核心矛盾:通缩螺旋固化,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尽管泡沫已破,但日本企业与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未被有 效清理,形成大量“僵尸企业”“僵尸银行”。与此同时,家庭与企业持续去杠杆、压缩支出,导致私人 部门投资与消费意愿持续低迷。在此过程中,通缩预期(CPI连续负增长)不断自我强化,抑制信贷需求与 价格恢复,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政策应对:日本政府原本对危机并未有明确认知,对于政府干预经济持谨慎态度。直到1993年才如梦方 醒,开始连续多年出台刺激性财政政策, 决定通过扩张财政来刺激经济,140万亿日元公共工程,但效果 有限(GDP乘数仅0.3);而后开始叠加货币政策,且力度不断加大,2001年开始启动量化宽松。
市场表现:1993年,日经225指数上涨2.91%,东证指数上涨10.07%。市场出现了短暂的中兴。 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已经开始衰退。1993全年GDP现价同比仅增长0.7%,较1992年进一步显著下滑,反 映经济动能衰竭。CPI同比仅1.3%,远低于80年代水平。核心通胀持续低迷,主因需求疲软及企业降价去 库存,远低于央行目标。失业率2.5%,PPI全年负增长,衰退迹象持续。 政策动向:财政政策不断加码:1993年9月追加6.2万亿日元刺激,重点投向公共工程,试图对冲地产泡沫 破裂影响。货币政策持续宽松: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央行通过购债释放流动性,M2同比增速维 持在3-4%,但信贷传导机制受阻,企业借贷意愿低迷。
本阶段可细分为全球化牛市(2004-2007)和后危机时代(2008-2012)两个阶段。 核心矛盾:2004-2007年,中美经济高增长,外贸与工业化加速,带动全球中间品、装备、精密零部件需求旺 盛,日本上游制造链受益。小泉改革(包括金融体系整顿、邮政民营化、公司治理改善)推动效率提升、强化海外 投九游娱乐NineGame资者信心。2008-2012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需骤降,严重冲击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骤降 16.4%;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带来额外经济与产业链震荡,短期内加剧不确定性。 政策应对:2004-2007年,小泉改革启动。2008-2012年,QE加码(购债规模扩至80万亿/年),零利率政策持 续,灾后重建投入23万亿日元。
市场表现:2004年,日经225指数上涨7.61%,东证指数上涨10.15%。市场延续反弹。 日本经济:日本经济走向回升。2004全年现价GDP同比增速为1.0%,GDP同比转正。反映经济动能有所 好转。PPI,CPI同比全年向上震荡。但核心CPI全年接近零增长,企业定价能力弱,居民消费意愿低迷, 经济仍处于通缩。12月失业率达4.7%,相对有所好转,经济企稳信心增强。 政策动向:零利率政策延续:2004年政策利率保持0%,日本央行通过购买国债维持流动性宽松,10年期 国债收益率全年在1.25–1.80%区间窄幅波动。尽管货币供应稳定,但通缩未缓解,反映政策传导效率低 下。此外政府债务率持续攀升,财政压力显现。
本阶段可细分为安倍经济学期(2013-2019)和日特股行情(2020至今)两个阶段。 核心矛盾:2013-2019年,顽固通缩与工资停滞并存,企业手握巨量现金却不愿扩张,政府债务已超GDP 两倍,财政刺激边际效用递减,增长引擎几近熄火。2020年至今,主板仍有四成公司长期破净,治理效率 低下导致外资持续折价,叠加全球加息与日元贬值,外资要求治理折价补偿;政府债务仍高悬于GDP之 上。 政策应对:2013-2019年,QQE负利率+治理改革,破净公司强制提ROE,银行估值翻倍。2020年至 今,东证治理新规+财政货币协同,外资回流六万亿日元。
行业轮动:领涨:海运,保险,电子设备。领跌:陆运,造纸,空运 ,涨跌归因:一方面,日本龙头企业在全球技术标准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丰田在混动领域的核心专利 占全球约60%构筑起深厚的技术护城河,在全球新能源转型背景下具备持续议价能力,支撑股价重估;另 一方面,部分制造企业因产业链外迁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虽然转移实现了产能全球化,但叠加人力和物 流成本上升,整体制造成本反而上行约30%,阶段性压制中下游企业盈利预期,引发估值分化。
创新性宏观经济政策:日本在长期低增长、高负债与通缩环境下,进行了长达三十余年的非常规宏观经济政 策实验,从零利率、QE、QQE到负利率与YCC,最终于2024年开启政策正常化进程。
以货币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核心,于1999年率先实行零利率、2001年进一步启用量化宽松政策,2012 年在“安倍经济学”推动下开启QQE政策,2016年引入负利率与YCC,进一步加码政策宽松性、刺激经济活 力,直至2024年退出非常规回归正常化进程,长达三十余年的宽松周期告一段落。
以财政政策为辅:90年代泡沫破裂后日本内阁长期依赖财政刺激,90年代起实行多轮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支撑 经济,2000年代虽尝试整顿,但金融危机后再度加码支出,2013年后“安倍经济学”强化财政扩张,2020 年代延续高支出以应对疫情与地缘挑战。
偶有汇率干预:自1985年广场协议起,日本多次通过市场干预应对日元升值压力。1990年代与2000年代前 期频繁干预,2010年后则趋于低频、应急式操作,配合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政策调节汇率预期。
常规调控到非常规干预:日本央行的基准利率政策经历从高利率紧缩到超宽松乃至负利率的重大转变。
政策回顾:1980年代末泡沫经济时期,为抑制资产价格过热,日本逐步将官方贴现率上调至6%以上;泡 沫破灭后,为应对长期通缩与经济停滞,自1990年代中期起持续降息,1999年正式实施零利率政策。此 后,日本央行在2001年引入QE,将政策重心从利率转向流动性供应;2006年短暂回归正利率,但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后再次降至接近零。2016年起,日本更进一步推出负利率政策。
效果评估:日本持续30余年的宽松周期显著压低融资成本推升金融资产价格,但对实体经济复苏和通缩治 理效果日益递减,埋下资源错配与资产泡沫隐患。利率长期处于接近零的区间,一方面削弱银行盈利能力 与风险定价机制,形成金融抑制;另一方面利率工具的实效边际递减,被迫转向依赖其他工具如QE等非常 规手段来维持通胀目标与经济稳定。2024年政策转向加息,虽试图恢复利率的价格功能,但进度迟缓。